 手机访问:wap.265xx.com
手机访问:wap.265xx.com如何理解冯唐的《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的结局?
才读完 看文中好像最后是“我”最后见了朱裳 然后掏出了生殖器打飞机么 我不是很理解为什么最后要做这样一个动作 能有人来帮我解释一下这个是想表达什么吗→ 。→PS:我很喜欢的就是最后桑保疆威胁时“我”说的那句话 :“懂,你就走,不懂,你就滚。”
一个男生,在幼稚年纪遇到了心仪的姑娘,平时如何睡女人在她的面前也是害羞状,比如不敢告白。这是种纠结,表达不出我爱你,离开你了,不如痛苦地表达,不是为了你高兴而是为了你心痛。
【1】或许人在面对离别的时候有放大招的潜能,唯恐一离别就会造成终身遗憾。
【2】于是,小说最后不断重复“只差一句话,只差一句话。”而当秋水见到朱裳后便说“明天就到别的地方上学了,想最后对你说句话。”紧接着就做出出格的举动,这对于平日里小心翼翼仰望朱裳女神的秋水来说是不可想象的。面对离别,面对着复杂纠缠的情愫和遗憾,或许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吧。
【3】嘻笑于冯唐的流氓语言,却感怀于故事的结局。就这样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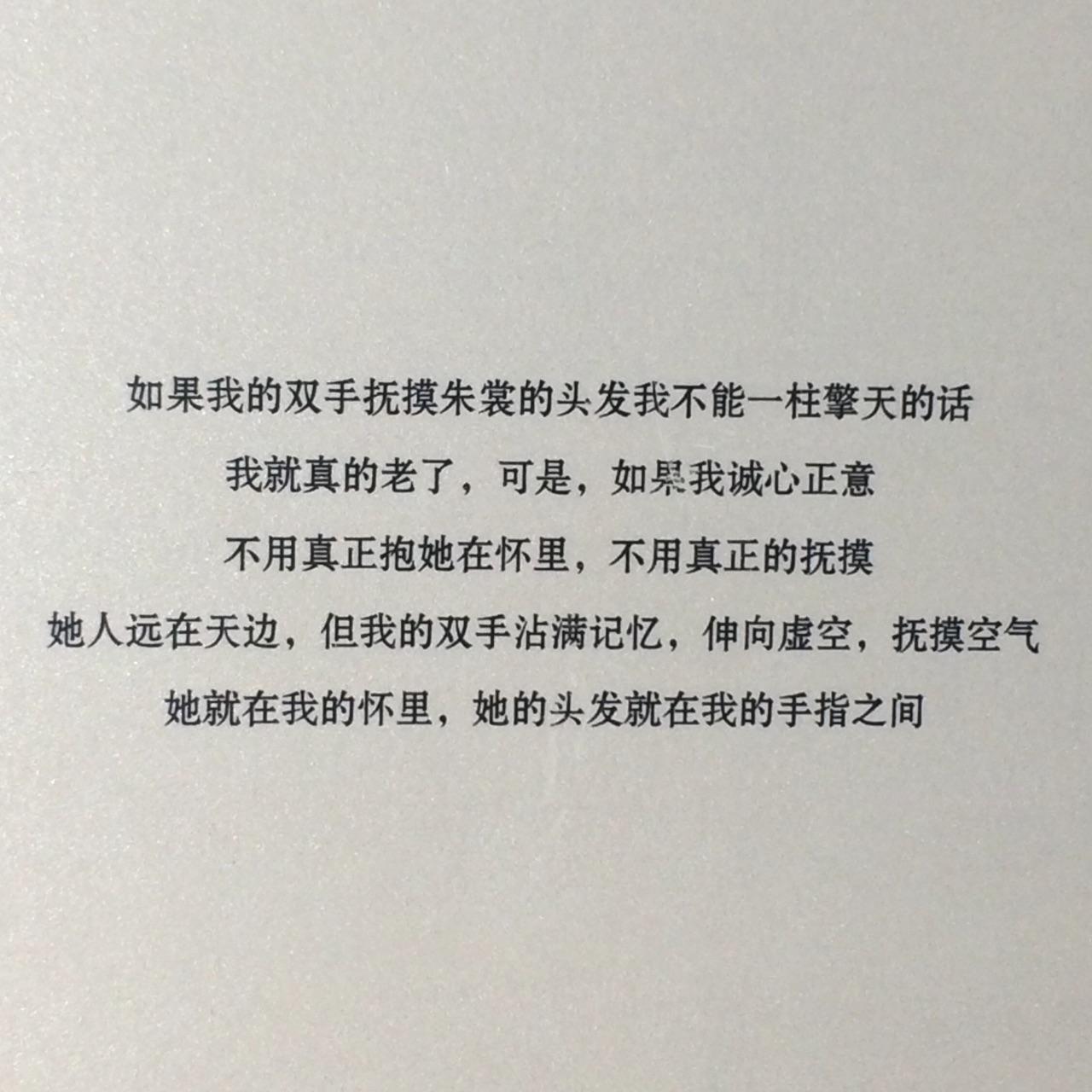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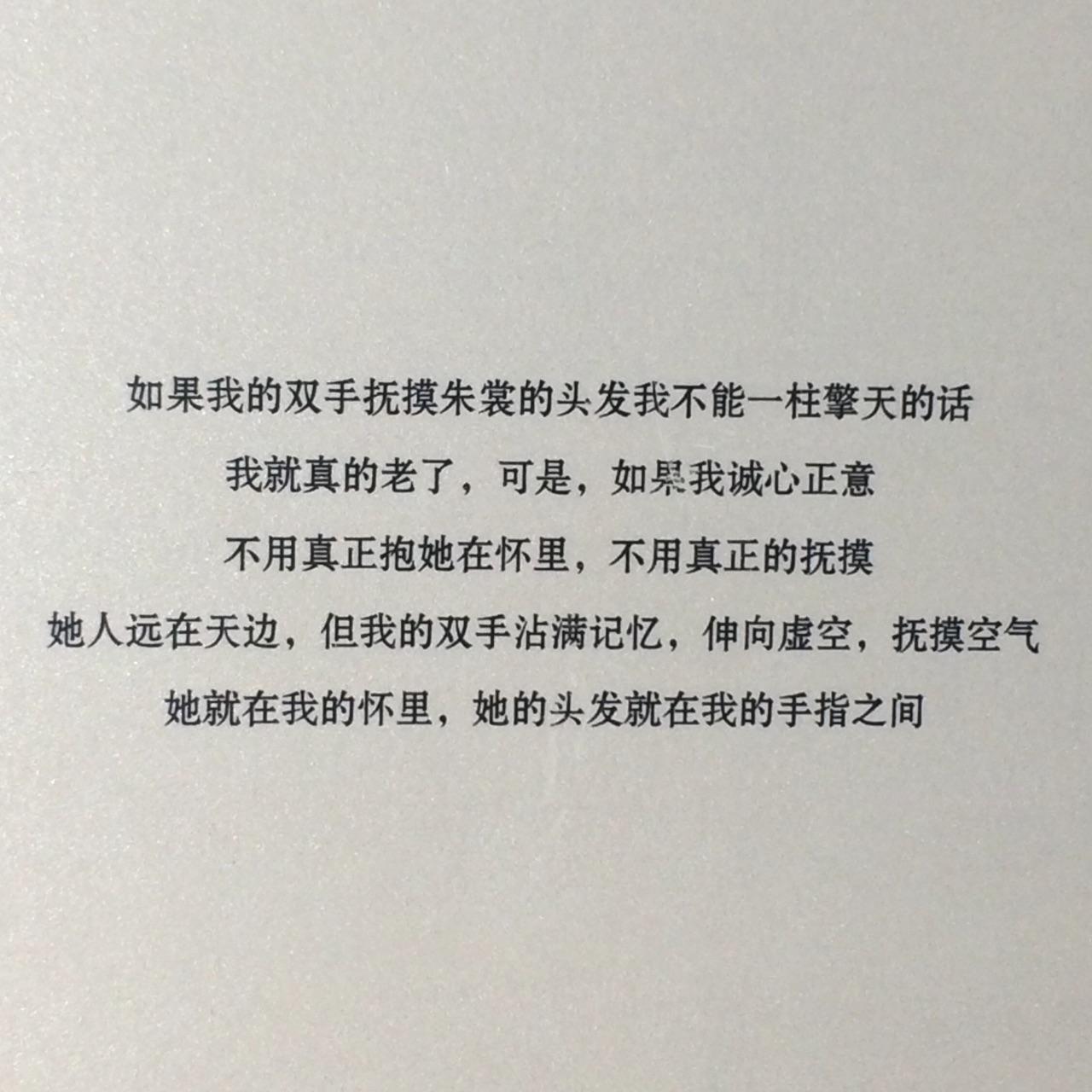 以上
以上
只差一句话 差的是对心爱姑娘的表白 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 于是做出的出格的举动 其实也算流氓方法的表白。
个人理解 随便看看就行
MD一百年前就四处推荐冯唐的东西,这几天无心复习,先是用手机连夜把一个小随笔集《猪和蝴蝶》看了,然后又下载了《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的电子书今天一口气读完。之前其实并不特别喜欢一些作家惯用以至有点用烂的“臭贫重口”+“(特别地)牛逼之气呼之欲出”的风格,感觉虽然读起来有种类于意淫的快感,但是读完之后却没有让人往复涵泳、回味无穷的感觉。通俗地讲,基本类似于av,让你爽一下后就没什么用了。理论地讲,就是没有触动到精神层面、没有在内心深处引发共鸣。刚开始读冯唐时,大抵也是抱着复习不进去找部比较易读的书消遣一下,但是读着读着,逐渐感觉到这些“臭贫粗口+牛逼之气”的文字在不自觉间渗透了时间浸润到心灵,于是有些不淡定了。
“朱裳”或是《朱裳》,如冯唐在后记中指出那样,本来是一部两三万字中篇,作为雏形发展成了《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这部长篇,于是“朱裳”这个形象和故事的其他部分似乎契合地并不是十分自然:首先不像一些其他人物“老流氓孔建国”、“张国栋”、“桑保疆”那样有血有肉有真实感,其次和这些人物的互动关系有点若隐若现、不太真切。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作家刻意而为,但似乎恰恰是“朱裳”的这种略微Blurry的呈现成就了这篇小说——至少对我而言。
冯唐在序言中说,“《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的写作动机非常简单,在我完全忘记之前,记录我最初接触暴力和色情时的感觉。”确实,书中呈现了大量对于暴力和色情的感觉,如果没有对朱裳的“特殊呈现”,这本书或许也就止于“暴力和色情”仅有的刺激感与爽快感——借用冯唐自己在《猪与蝴蝶》中的比喻,这道菜里就只剩辣椒、没有鸡肉了。虽然写到朱裳时冯唐似乎也并没有全然避开暴力色情臭贫重口的元素,但读完这本书却觉得朱裳这个形象似乎有点不溶于这一锅满是辣椒油的浓汤,反而让人感到她在“秋水”心中的特别之处:虽然暴力和色情的元素不可避免无可厚非地溢满沸腾在青春这口锅中,但对朱裳的那种向往(而非追求)却始终无可动摇地存在于“秋水”心中——这种向往显然不是“纯洁的”“柏拉图的”,但其中充满“纯真”与“温暖”, 读下来竟是如此令人感动。而这种纯真与温暖,反过来也并不是要去“消除压抑”所谓的“暴力色情”,而是以某种方式协调地共存着,而小说的结尾将这两者以一种“新奇出乎意料”的方式结合在了一起,留下一种难以言说的趣味(或恶趣味?)。
又如冯唐在后记中说,“《朱裳》……过了十几年重看,文艺腔很重,幼嫩可笑,但是反映当时心境,是好的材料”,如果只有这种“文艺” 的“朱裳”,那么这篇小说又要沦为沉迷于另一类意淫的“青春纯爱小说”了——全是鸡肉没有一点辣椒未免久腻而无味。而冯唐好就好在人和笔都已老道,于是一方面不必有顾忌,一方面写得有底气,再加上《朱裳》作为当时自己心境的记录,似乎给小说增添了不小魅力。带有一定回忆性的记叙将现在的想法和认识与当年的心境和情绪穿插在一起,书中暴力色情臭贫重口的文风和在关于朱裳的那些“纯得不正常的”的“文艺腔”、“情诗”、大段心理描写等等穿插在一起,这些基调上、色彩上的对比与分离给人出奇的真实感与自然感,于是也愈发动人。突然想起上周西方艺术史在讲到十五世纪北欧艺术时提到的那种特殊的“写实主义”,通过把“神”“圣人”的形象画成普通人的两倍大小、或是把“天使”“圣人”画成纯白而把凡人画成彩色等,来实现其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从而达到一种诡异的“impressivelyreal and oppressively ideal”的“Realism”(如 Hugo van der Goes 的 Portinari Triptych,Jan van Eyck 的 Ghent Altarpiece 等)。朱裳就像是这么一个“天使”,对她的美好的描写如同皮革马利翁或无崖子的刻刀,带着某种有些 oppressively ideal的痴迷。或者说,还是以 Jan van Eyck 的 Ghent Altarpiece为例,朱裳的那种感觉更像是那个被上了一半色的天使——西方艺术家用这种不寻常的着色来实现具有宗教意义的Realism——朱裳身上这种Blurry的设定似乎实现了一种 impressively real的 “怀想青春”的 Realism。这种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手法根源于所描述对象本身所固有的“理想化”与“非真实”,如天使和圣母,如少年心中的“绝代尤物”,因此,当冯唐如辛弃疾感叹“为赋新词强说愁”般感叹“文艺腔很重,幼嫩可笑”时,并非试图去否定“文艺腔重,幼嫩可笑”,反而是通过这种“文艺腔重,幼嫩可笑”(oppressively ideal)来呈现“秋水”那 impressively real 的十八岁。
『我从枕头底下拿出来藏着的一包大前门,反锁了宿舍门,点上一棵给张国栋,自己再点一棵。我坐在床铺前的桌子上,向张国栋表白,希望他能理解:
“我坐在朱裳身边,如果天气好,窗户打开,风起来,她的发梢会偶尔撩到我的脸,仿佛春天,东三环上夹道的垂柳和骑在车上的我。”我看着张国栋,接着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
朱裳坐在我前面而不是旁边,散开的黑发在阳光下碧绿通灵。原来系头发的红绸条随便扔在课桌上,绸条上有白色的小圆点。当她坐直听讲的时候,发梢点触我的铅笔盒。当她伏身记笔记的时候,发梢覆盖她的肩背。
我拿开铅笔盒,左手五指伸展,占据原来铅笔盒的位置,等待朱裳坐直后发梢的触摸,就像等待一滴圣水从观音手中的柳枝上滑落,就像等待佛祖讲经时向这里的拈花一笑,就像等待崔莺莺临去时秋波那一转。
我没想到,那一刻来临时,反应会如此剧烈:五颜六色的光环沿着朱裳散开的头发喷涌而下,指尖在光与电的撞击下开始不停地颤抖。』
……
2011年3月6日
别想太多,别理解太少。之前这位流氓作家把这件事给了一个结尾。注意:结尾不等于结局和结束。
最近更新汽车资讯
- 哲学沙龙
- 高原痛风临床研究
- 快播插件(SPSS无法启动因为应用程序的并行配置不正确)
- 教育部2021年工作要点:加强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 【陪你母乳喂养】 哎哟喂,没生孩子也能泌乳?
- 重组家庭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妹可以结婚吗
- 非现役人员生活待遇经费保障与管理探析
- 《发展心理学·从生命早期到青春期》基础理论读书笔记--结合教育动画的相关研究
- 2023届河南省郑州市(二模)高中毕业第二次质量预测语文试题及答案.docx
- 《那片星空那片海》全集剧情简介 分集剧情介绍
- 给6-15岁男孩女孩的精选主题书单(分性别,暑假必备)
- 优秀家长家庭教育经验分享5篇
- 郭洪雷:汪曾祺小说“衰年变法”考论
- 章子怡汪峰吵架原因 章子怡与汪峰吵架事件详情
- 情感故事:不回家的女人
- 道德伪善的教育学思考
- 2018级高职医学影像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以国家之名的罪恶——评德国影片《窃听风暴》
- 影视传播范文10篇
- 九天揽月一一敢峰证明四色定理之谜
- 挪威流产或人工流产后妊娠的妊娠间隔和不良妊娠结局(2008-2016 年):一项
- 好看的美剧排行榜(12部高分高质美剧推给你)
- 解放思想大讨论心得体会
- 长谈 | 内蒙古电影新浪潮:现实的结构与质感
- 美国《国家性教育标准》及其启示(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