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机访问:wap.265xx.com
手机访问:wap.265xx.com为什么农民不种价值高的作物?
比如西瓜哈密瓜草莓等这种水果,明显价值利润都高于像水稻小麦等这种传统农作物。为什么还有很多农民去种水稻也不愿种西瓜。
“想要说服这里的回族农民,那可真不容易。”
在二十世纪末的宁夏西海固,张承志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当时,这位黄土高原上的知名作家在笔耕之余,正热情投身于另一项事业,那就是劝说当地农民放弃土豆,种植橄榄,改造环境,脱贫致富。
然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这辈子都没费过这么多口舌。从村干部到林业局,从学校的老师到寺里的阿訇,能说上话的他都说了个遍,就是没人听。
张承志无奈地总结说,这里的农民实在穷惯了,苦惯了,倒霉惯了。
别看这三个“惯了”的说法很文学,背后其实有深刻的道理。
2007年,一部名叫《大明王朝1566》的电视剧上映,收获了很多好评。这部剧的剧眼,也就是剧情中心和主要矛盾,叫做“改稻为桑”问题。
直到今天,剧里的改稻为桑为何不成,依然是许多剧迷津津乐道的一个问题。
给不了解这部剧的读者简单解释一下:在《大明王朝1566》的第一集,明朝政府核算收支,发现入不敷出。内阁首辅严嵩向嘉靖皇帝提议,命浙江30万亩稻田改种桑树,造丝绸通商补贴国库。皇帝当即拍板同意,全剧由此拉开序幕。

 改稻为桑这件事是电视剧虚构的,历史上并没有真实发生过。但是,这个虚构的事情确实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非常耐人寻味,就成了流传很广的名梗。
改稻为桑这件事是电视剧虚构的,历史上并没有真实发生过。但是,这个虚构的事情确实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非常耐人寻味,就成了流传很广的名梗。
网上对改稻为桑失败的原因已经有了很多分析,例如以严嵩为首的官僚集团腐败严重,浙江地主商人利欲熏心,改稻为桑会加剧土地兼并,伤害农民等等。
就电视剧和明朝历史来说,这样的分析或许已经足够深刻。但我们不妨追问一句,如果脱离了明朝中期的背景,改稻为桑还是件难事吗?
换句话说,换个时代,换个地区,换个政府,换个经济模式,农民就会欣然接受新作物吗?
答案是否定的。最直接的反例,就是我们开头讲到的宁夏西海固。
其实不只是宁夏,不只是中国。从拉丁美洲到东南亚,从非洲到中亚,过去几个世纪当中有无数这样的例子。类似的事情到今天也在发生。
在工业化之前,全世界农民生活的环境是类似的,遭遇的困境也是类似的,在改稻为桑面前,他们的思维方式也是类似的。
苏联作家高尔基有句名言:“哪里的农民都一样。”他对农民的这些看法,没少遭到来自有着激进传统的俄国知识界的批评。
然而,这是出身贫苦的高尔基通过亲身经历得到的感悟。从法国到俄国,再从俄国到中国,全世界有那么一种通用的东西,是农民不约而同的共识。
这种共识,叫做经济伦理。

 讲经济伦理之前,我们先谈一点经济史常识。
讲经济伦理之前,我们先谈一点经济史常识。
请问,人类吃饱饭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最接近标准答案的回答是,分地区讨论。
西欧和北美在19世纪末才摆脱饥饿的威胁,东欧和拉美是在20世纪中叶,亚洲是20世纪末,而非洲要等到本世纪中叶。
也就是说,我们人类当中来自最先工业化的那批人,吃饱才不过一百来年;人口占比最大的那批人,吃饱还不到半个世纪;人口增速最快的那批人,还没吃饱饭。
在农业社会形成以来约一万年的历史当中,这几十上百年的时间实在微不足道。
成千上万年的农业社会史,就是饥饿的历史。充当社会主体的食物生产者,也就是农民,一直在忍受饥饿的驯化。
在变幻莫测的环境和层出不穷的剥削当中,传统社会的农民形成了自己的经济伦理。这种伦理没有什么复杂的理论体系,它的核心只有一个词:生存。它的第一法则也只有一个词:安全。
在农业生产当中,农民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收获够不够自家的口粮,够不够来年的播种,而不是余粮能换来多少钱。
农民关心的不是提高产量发大财,而是避免歉收不挨饿。现代经济学“理性人追求边际量”的基本假设,在古代农民身上根本不适用。
这就是“改稻为桑”的核心矛盾所在,如果改种经济作物让农民对所得粮食的下限失去把握,再高的利润都很难让他们冒这个风险。
最典型的例子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非洲殖民地。当时,英国殖民者为了创造利润,让殖民政府收支平衡,开始大面积鼓励种植经济作物。
在英属东非,乌干达农民比较顺利地接受了棉花种植,而肯尼亚农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原因非常简单,乌干达人的主粮是大蕉,能和棉花错开季节生产,而肯尼亚人的主粮是玉米,和棉花种植有冲突。是否影响主粮种植,就是农民决策的唯一标准。
在英属西非,殖民者推广的经济作物是可可。可可在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的农民当中推广较快,但是在塞拉利昂农民当中举步维艰,背后原因也是一样的。
土地、水源、劳动力,只要经济作物在这三样当中的任何一样和农民的口粮发生冲突,增加了实质性的风险,“改稻为桑”就会无比艰难。

 上面非洲的例子来自殖民地时期,也许有的读者不能信服,我们再举两个独立国家的例子,而且这一次不是粮食作物换经济作物,而是旧粮食换新粮食。
上面非洲的例子来自殖民地时期,也许有的读者不能信服,我们再举两个独立国家的例子,而且这一次不是粮食作物换经济作物,而是旧粮食换新粮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三十年,泰国和菲律宾是东南亚经济发展较快的两个国家,两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农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20世纪60年代,新品种水稻来到了东南亚。相对当地农民种植的旧品种,新品种的产量上限提高了两倍。乍听上去,这么高的产量根本无法拒绝,然而泰国和菲律宾农民用实际行动投了反对票。
在菲律宾,农民不愿意种新品种的原因在于,新品种对水源的要求很高,而当地降水不稳定,这就意味着产量不稳定,下限可能低于旧品种,让农民无法接受。
泰国农民发现,新品种水稻对犁地的要求更高,想要种植就必须雇用外村的拖拉机手。农民们认为,陌生的外村人不可信任,意味着巨大的风险,他们宁愿种植旧品种,继续用本村的牛来犁地。
从这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农民忌惮的并不只是“改稻为桑”,如果改换作物可能威胁口粮,增加风险,打破了安全这条第一法则,就算利润再高,“改稻为稻”,都很难推广。
近代以来,许多政府拿出软硬兼施的手段,试图挑战农民根深蒂固的安全守则。在讨论那些成功的转型之前,我们首先来看看失败的例子。
看了这些例子,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古代农民对“改稻为桑”有着近乎本能的恐惧。
1944年夏天,一串台风席卷了越南。
洪水淹没了许多稻田,人们挨饿在所难免。按照往年的情况,凭借越南农村的互助和救济机制,这样的年景还是能熬过去的。
然而,这可是天杀的1944年,二战中的1944年。
1944年的越南名义上是维希法国的殖民地,实际上由日本控制。物资匮乏的日本军队在占领区没收余粮,并且强迫农民种植黄麻等军用作物。
在之前几年,这样的日子还可以过活,种黄麻的农民还可以得到比种粮食更高的收入。到了台风突袭的1944年,一切都变了。
饥饿的越南农民吃掉了一切可以吃的东西,在1944-1945年间,多达200万人饿死。日本人的“改稻为桑”打破了越南农村的保险机制,造成了巨大灾难。
在殖民主义的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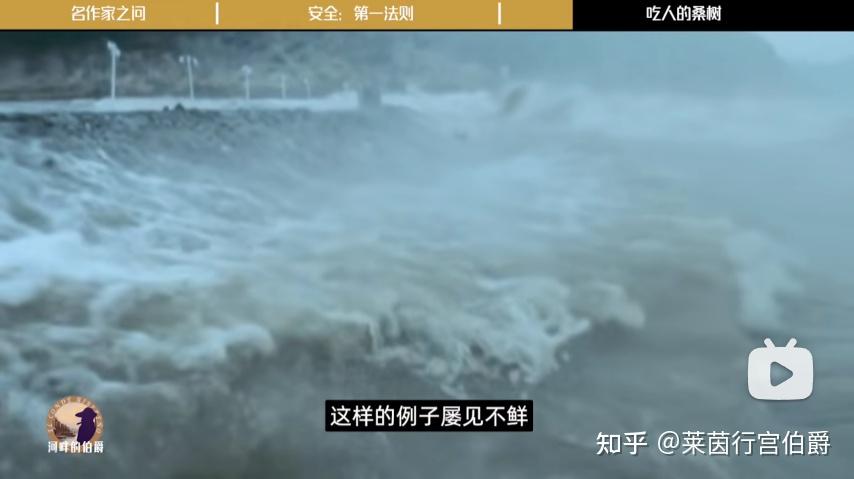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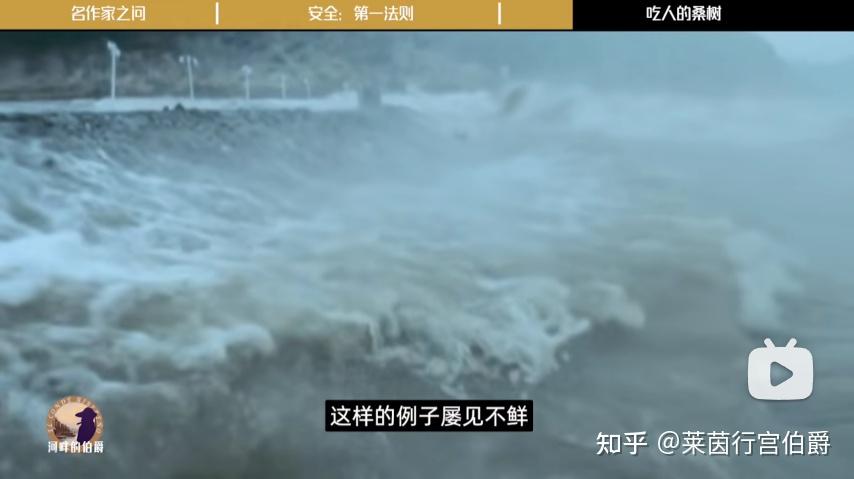 1770年,英国殖民者的地税改革、谷物垄断、棉花和罂粟种植政策引爆了孟加拉大饥荒,近1000万印度农民饿死。
1770年,英国殖民者的地税改革、谷物垄断、棉花和罂粟种植政策引爆了孟加拉大饥荒,近1000万印度农民饿死。
在两个世纪之前的“西印度”,西班牙人要求印第安人放弃玉米,改种殖民者喜欢吃的小麦,水土不服和技能不熟练也在墨西哥引发了饥荒。
古代农民的经济伦理和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形成了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在资本的世界当中,利润至上,风险是理所应当的代价,只要利润足够,就没有不可以冒的风险。
对于古代农民来说,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风险就是洪水猛兽、恶鬼煞神,不管有多大的利润引诱,都不可以轻易触碰。
殖民主义的降临,撕碎了古代农村的自然经济,打破了古老的互惠机制,把大自然和人变成了商品,给他们冠以原材料和劳动力这两个新名字。
但是,殖民主义又不能立刻创造出一个工业化的新世界,在这个名曰现代化的漫长转型过程当中,无数农民充当了代价。
正如马克思所说:“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殖民者的“改稻为桑”就是一个剥夺农民生存保障,进而夺取其生产资料的过程。用利润取代安全作为第一标准,本身就是人类经济史上的一次巨大变革。
农民的经济伦理遭到了颠覆,古代农民追求安全,就和现代资本追求利润一样,是颠扑不破的基本逻辑。不让资本逐利会杀死资本,逼古代农民逐利会杀死农民。
但是,说“改稻为桑”只是在殖民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会造成恶果,也是不公平的,说到底,这件事反映的是社会客观规律,不完全是意识形态问题。

 20世纪60年代,访美归来的赫鲁晓夫开始推行一项雄心勃勃的农业改造计划,也就是著名的“玉米运动”。
20世纪60年代,访美归来的赫鲁晓夫开始推行一项雄心勃勃的农业改造计划,也就是著名的“玉米运动”。
在这场运动当中,苏联官僚们无视各种自然社会条件的不适宜,强行推广玉米种植,终成一场闹剧。赫鲁晓夫本人也因此被嘲讽至今,成为知名的“苏穗宗”。
不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赫鲁晓夫时期也有一场相对成功的“改稻为桑”运动,那就是苏联的中亚棉花种植计划。
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一直在中亚地区推广棉花种植。在20世纪,中亚成功超越19世纪三大传统产区(南亚、东北非、北美)成为世界第一大棉花产区。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的计划,也造成了许多未曾预料的后果,例如对咸海环境的破坏,以及中亚官僚的严重腐败。
无论如何,对于普通农民来说,“改稻为桑”意味着风险。至于这种风险的来源是大自然,还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官僚主义,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按照传统方式种植粮食作物,能够给予他们最大的抗风险能力,让他们最小程度免于饥饿和破产之苦。这是一种笨拙,也是一种积累了几千年的智慧。
所以张承志说,西海固的农民不愿意种油橄榄,只是因为他们穷惯了,苦惯了,倒霉惯了。安全至上,就是他们夹在经文里的书签。
蝗虫的滋味、台风的滋味、火山灰的滋味、地主豪绅强取豪夺的滋味、殖民商人欺骗勒索的滋味、无能官僚蛮横盲动的滋味,农民们尝过太多了。
“城里人”不理解农民为什么不敢创新,农民们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不理解。
站在农民的角度,他们经济伦理并不难理解。真正难做到的事,就是站在农民的角度本身。
现代人读历史,常常代入精英立场而不自知,自以为是客观的上帝视角。这种情况我见过很多,自己有时也会犯。唯有不断学习、反省,才能戒之改之。
如果真有“利国利民”的“改稻为桑”,怎还会有“苦甲天下”的“西海固”们?


上一篇:因“尺度问题”被禁播的5部剧,我猜你就看过最后一部,不信你看
下一篇:不要以今论古,谈一谈唐高宗李治娶武则天的伦理问题
最近更新生活资讯
- 反转再反转,这部科幻末世灾难片真的爽
- 快捷指令sky电影捷径库
- 2021《自然》年度十大人物:塑造科学,造福社会
- 千里单骑救萝莉却被捕,“正义使者”成了谁的牺牲品?
- 浪漫爱情励志人生 最震撼人心的十部日剧(图)
- 短篇小说(家庭伦理)
- 推动农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协调发展
- 资料:成奎安电影作品《灯草和尚》(1992)
- 稻盛和夫《活法》1
- 合肥市第六中学2019-2020学年下学期2019 级高一年级线上线下教学衔接学
- 全网的电视剧,电影和动漫无偿观看(每年的都有哦)
- 理想国
- 刺激!梅州首部限制级伦理微电影《幻镜》网络首映!
- 男人为何迷恋女人胸部?
- 陆小曼与林徽因:都是富养的女儿,差别在哪里?
- 问题已被解决?
- 看了多少烂片,才找出这92部经典!
- 金高银:怎么从拿8个电影奖的怪物新人沦为了被众嘲的“资源咖”?
- 猎天下第2部:河阴之变
- 封神演义读后感100字(五篇)
- 又一部岛国神作,堪称校园版《权力的游戏》!
- 【全面解读】2022年以后,再无“国产”BCBA?
- 鬼文化(商代的帝王文化))
- 豆瓣9.2分年度第一佳片,每一秒都是夏日初恋的味道
- 社会的重器:性侵犯罪信息统一查询平台,还校园一片蓝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