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机访问:wap.265xx.com
手机访问:wap.265xx.com小偷家族:主动选择的家人,羁绊更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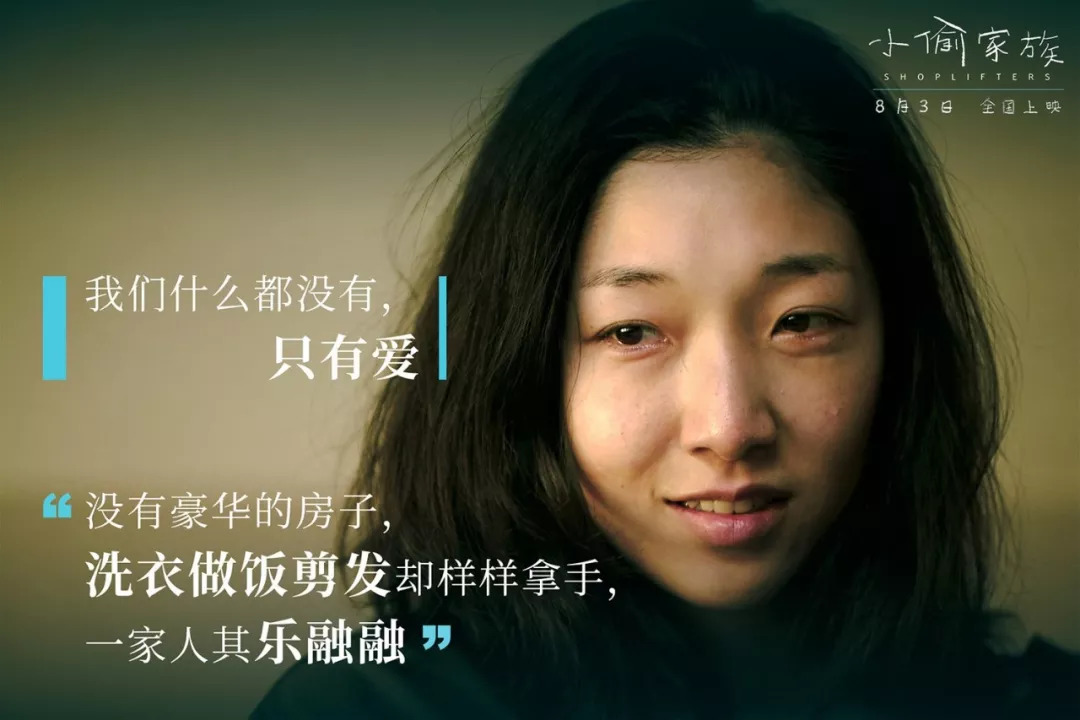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们什么都没有,只有爱”。是要对这部《小偷家族》产生了多大对误解,才能写出这样的电影宣传词。底层的色调从来不是温情的,它关乎一种活下去的欲望。这个世界对贫穷者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误解和想象,每一次试图将电影镜头对准流动在底层的蝼蚁时,却又不自觉地将中产阶级的模糊化的审美强加上去。
是枝裕和或许是个例外,1962年出生于东京,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的他,先是进入纪录片的拍摄,1993年曾拍摄记录片《当电影映照时代:侯孝贤和杨德昌》。幼时的成长环境、成年后纪录片的拍摄经验以及对台湾文化的特殊喜爱与研究,共同造就了是枝裕和不同于其他导演的拍摄意识。
是枝裕和在电影里呈现出的是对任何社会性议题保持着一种无解的态度,他无意交出任何解决方案,也更没有去批判任何处在某种位置上的个人,这种冷静以及客观在很多观众看来或许过于冷酷,在这个没有人需要负责人的社会,我却觉得,是枝裕和这样地阐释,打破了原先规范而又区隔的人际关系。恰恰是冷漠的凝视,重新在人与人之间,塑造了一种真实的温度。
这种意识,在是枝裕和2004年拍摄的剧情片《无人知晓》得到了最好的阐释,即使如今的《小偷家族》也难以企及。尽管《无人知晓》暴露了身为导演更多的粗砺感,而《小偷家族》却反映着走过许多岁月、拍摄许多电影之后的驾轻就熟。
如果有一天你被抛弃了,你要如何活下去?《小偷家族》与《无人知晓》一样,讲述的都是被抛弃者的故事,但两者表达的视角非常不同。《无人知晓》讲述的是四个被抛弃的孩童的故事,而《小偷家族》则要讲述的是“被抛弃的人——被抛弃的人组成的家——被抛弃的人抛弃组成的家”这样一个环环递进的故事,是在这样的故事推进中,是枝裕和将问题意识不仅停留在“被抛弃者该如何活下去”这样一个单向性的属于少数人的问题,而是一个“我们人与人之间究竟该如何创造更真实的连结”的广泛的针对所有人的社会性议题?
是枝裕和在接受韩国中央日报采访时,曾表示:“家庭随着共同体文化的崩溃而消解。不仅没有成熟到接纳多样性,还渐渐向地域主义靠拢,剩下的只有国粹主义,日本不承认历史的根源就在这里。我对亚洲邻国充满歉疚。日本也必须像德国那样道歉。但由于一直是同一个政权掌权,我们失去了大部分的希望。”
“没有成熟到接纳多样性”的,岂止日本一个国家?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是枝裕和,也许是他隐隐戳破了中国传统家本位的冷酷实质,正如《小偷家族》里的人是因为钱而维系在一起,十几亿中国人仅仅是因为“家”维系在一起,但这种维系根本上是一种幻象,是一种关于“家”的幻象。我们以为家内充满了温暖、奉献、关爱,实质上,那更多的是一种利益的勾连,从一个家的幻象走入另一个家的幻象,却从来不曾先置身事外地问一次;我们想要的家,究竟是什么样子?
而所谓的“日常生活”,又究竟指涉的是“何种生活”?
这也是为什么更多的人从影院走出来之后,却开始咒骂起是枝裕和,他道出了人的某种渴望却又不给予一条通向渴望的明路,叫人不得不承受这生活之中的痛。
海德格尔一直认为:“人是被抛进这个世界里的?”所以他觉得寻求“栖居”是人一生最本质性的追求,落在日常生活里这就是关系的建立,但时间推进之后,日常生活却出现了一种本末倒置,关系本是为人的栖居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办法,最终却变成了为了关系的连续我们不得不一再攀附于关系,却忘了,栖居的追求是不可更改的,但关系的模样却可以是多样化的。如果家是攀附于确定性的血缘关系,那或许在这个世界上自诩为智人的我们,迟迟没有走出狭窄而又自我封闭的遗传本能,那种从祖先的血液里带来对于自身基因优越性的承认却从无实质性的证明,而这悬而未决的历史性生成却没有突破时间的演进创造出更富崇高性的栖居?
所以,在《小偷家族》里,沙滩边的奶奶轻声说出了“谢谢你”,小男孩在告别之后,在公车上叫出了被期待已久的一个称谓“爸爸”。是枝裕和以一个逸出常人眼光常人生活之外的生活图景,以一个“家”的聚和散松动着人们对家的惯性认知,也以一种温柔的注目给予了一丝不易察觉地对“真实的关系”的肯定。
日常生活,是 “daliy life ”还是“everyday life”?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后期的研究就倡导从日常生活出发,通过对于日常语言的分析来探讨哲学问题。作为概念的日常生活,经由现象学家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强调人的具体经验(lived experience),到舒茨将生活世界引入社会学,后来社会学家芬克尔在此基础上突破传统的“家庭”、“小团体”等初级关系的狭窄范围,创立更为深入考察日常活动的经验研究的方法——常人方法学:关注核心的社会规则与“日常生活的结构”。而以上都仍然拘泥于宏观的总体性,并没有真正走入个体的微观生活,直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出来的“日常生活批判”,包括卢卡奇、赫勒、列斐伏尔、德波和塞托,从“日常”出发反思资本主义乃至现代性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深刻影响,可以称之为宏观思维插入微观生活的一把深刻的“刀”。
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正是在以上的历史生成中的艺术展演,“习以为常之蔽”,是枝裕和的电影是一种“日常生活”的言说,这种言说是一种揭露的过程,将原本宏观视角下遮蔽的微观非常态重新回到日常的范畴下,并以此来重新探讨对“日常”的定义。
在拍《奇迹》的时候,是枝裕和想着这是等女儿十岁时观看的电影,想要对说:“世界如此精彩,日常生活就很美丽,生命本身就是奇迹。”
同样将电影镜头对准日常生活,是枝裕和常常被称为小津安二郎的接班人,但他却认为自己在电影诉求上更多的来自于TBS前辈们的影响:编剧如山田太一先生,向田邦子女士,导演的话则是鸭下信一和久世光彦。但不可否认,与中国第五代、第六代导演们那种对于描述生活与历史之间关联的用力过猛,日本导演们真的在隐藏情绪,却以一种平和而又恬淡的镜头透露出来更多的深刻和思考有着天然的把控力。
不管是小津安二郎还是是枝裕和,他们都未曾站在制高点上试图以电影来指导观众生活,他们只是说:活下去吧,活下去吧,这样便很美。
正如是枝裕和所言:
“而我更想描述,没有英雄,只有平凡人生活的,有点肮脏的世界,忽然变得美好的瞬间。” 电影片段
电影片段
这个社会还会爱人吗? 不会,这个社会从来看不见人。
但,身为人,想要被人看见,先去看见。
上一篇:痛心!两岁男童被看护中心人员遗忘在车内9小时,发现时已死亡
下一篇:解读《疯狂动物城》电影绘本中的疯狂英语Chapter 18
最近更新影视资讯
- 韵府群玉
- 老年临终关怀护理集锦9篇
- 如何评价剧场版动画《和谐(harmony/ハーモニー)》原作:伊藤计划 ?
- 智人战胜尼人的决定性因素 是神灵崇拜与艺术品 在3万7千年前智人击败了远比自己强
- 沈阳参考消息(2017年1月11日)
- 密集架区密集架书库图书馆负一楼期刊阅览区中外文期刊图书馆一楼图书借阅区(A-H
- 费维光:脾胃病17方
- 土耳其身为伊斯兰国家,为什么允许“风俗产业”合法化?
- 高中教师教学反思
- 三观尽毁!90后公务员出轨50岁女上司,聊天言语暧昧,妻子怒举报
- 22应用心理学考研347 首师360有调剂院校吗?
- 铃木凉美女士,你仍期待同时收获怜爱与尊敬吗?
- 团建别墅 | 确认过眼神,是能疯一起的人!Boss,今年年会我们泡私家温
- 《归来》观后感
- 翻译伦理的重要性和译者荣辱观建设研究
- 高二语文期末考试测试题及答案
- 国医大师名单!在北京看中医该找谁,这下全知道!
- 这些年爱过的同人文(BG)
- 荷兰深陷风俗业?日本都要甘拜下风,为何能稳坐世界顶尖位置!
- 戴安娜25年前私密录像首次解密:自述性生活,全英国都被炸懵逼了
- 原创上官婉儿为什么必须死,她做的这件事太无耻,李隆基忍无可忍
- 「医药速读社」Paxlovid临床失败 礼来斥巨资引进Kv1.3抑制剂
- 她是韩国性感女神,靠出演“三级片”走红,今41岁韵味不减当年!
- 电影市场有望点燃 好莱坞大片排队上映
- 评荐《传染病(Contagion)》
